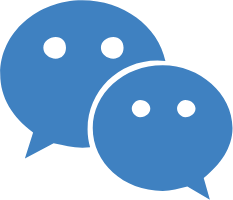新闻中心
张登科先生原创文章:太白山上,杜鹃绝唱~

“寒冬腊月哟盼春风,岭上开遍哟映山红”——这是197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中国儿童红色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插曲,歌词表达了对红军到来的热切期盼。那时我还正在读小学六年级,这部电影至少看过三遍。其中有一个场景今天还印象深刻:潘冬子与父亲重逢时,满山遍野绽放的映山红仿佛勇士的鲜血般鲜艳夺目,激发出国人心中的壮阔豪情,令众多观众热泪盈眶。映山红又叫杜鹃花,在那个时代人们把杜鹃花开视为不惧牺牲、勇于斗争的精神化身。

时光流转,六月初的西安古城暑气蒸腾,我们随“新舒沐自然能量之旅”踏上了太白山。在这片清凉世界,高海拔的奇花异草正悄然上演着生命的奇迹。行至海拔3500米的“天圆地方”,凛冽的山风裹挟着寒意,太白杜鹃、秀雅杜鹃、密枝杜鹃积蓄了整个冬春的力量,正于高寒绝域肆意盛放,将苍茫山野点染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天然画卷。

漫步山间,目光所及皆是摄人心魄的绚烂。未绽放的红色花蕾如燃烧的火炬,粉色的花朵似天边初凝的云霞。紫色的花瓣如丝绸般轻柔,或小巧玲珑聚成花球,或舒展如裙裾随风轻曳。在太白山最纯粹的阳光的熔炼下,每一种色彩的纯度都还原到极致。花海如潮,奔涌在冷杉墨绿的林带之下,形成“上绿下红”的奇观。更有那秀雅杜鹃,独踞于贫瘠的石海之上,以先锋小灌木的姿态,在阴坡岩缝间捧出秀中透雅的红艳,倔强宣告生命的奇迹。


杜鹃的绽放,是一场与严苛自然的无声对话。凛冽疾风与霜雪,是日常的磨砺;贫瘠稀薄的土层,是生存的常态。太白杜鹃以常绿小灌木之姿,将叶片浓缩于枝顶,于寒风中捧出奔放的花朵,在山脊上铺展成五彩斑斓的锦缎。

杜鹃花根系小、脆弱,缺乏可以吸收营养的根毛,难以为其提供赖以生存的营养。为了生存,杜鹃花细根就和土壤中的共生真菌形成菌根,该菌根具有很强的有机物分解能力,可以从土壤中的各种有机化合物中获取营养,为自己所用。每一朵迎风怒放的杜鹃花,都是千万年进化书写的生存智慧,印证着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箴言。

这绝域之花,亦承载着千年不散的文化精魄。自唐时李白于宣城见之感慨“蜀国曾闻子规鸟,宣城还见杜鹃花”,那哀艳的啼血传说便与花朵形影相随。蜀国国王杜宇精魂所化的子规鸟,年年泣血催耕,染红了遍野山花,让杜鹃成为壮烈与守望的永恒象征。杨万里一句“何须名苑看春风,一路山花不负侬”,道尽了其远离尘嚣、自在山野的孤高本真。

当又一次在仲夏登上太白山,那铺展于冷杉林下、石海岩缝间的杜鹃花、报春花、马先蒿带来的美妙观感,早已超越了植物本身。它们是冰霜中锻打出的生命焰火,是自然伟力与人文精魂在云端共舞的交响。每一片在寒风中微颤的花瓣,都在诉说:真正的绝美,生于险远;永恒的力量,淬自风霜。

高寒之上,生命以最浓烈的色彩击退荒芜——这惊心动魄的怒放,是花朵对高山的献礼,更是大地写给勇者的灼灼诗行。